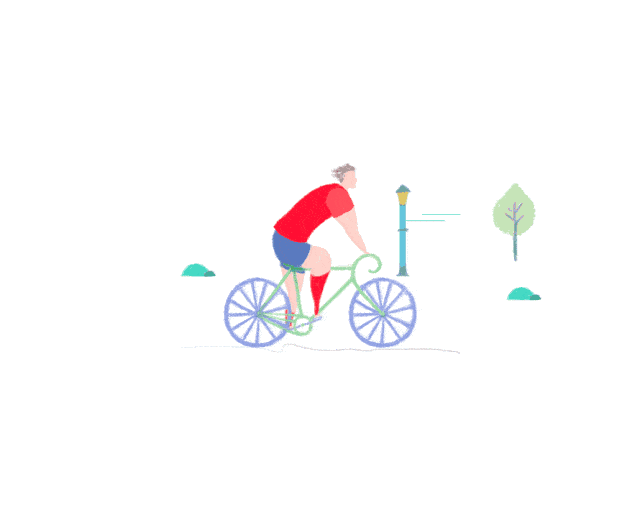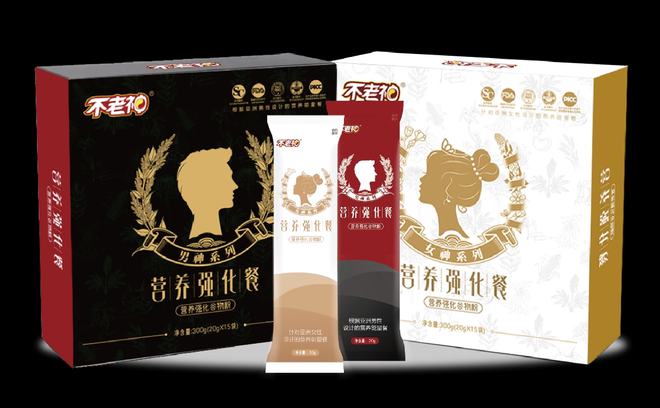他不太追求“鸟图”的美感,而是更关心图片是否清晰,能否分辨出是什么鸟。这是他观察和记录群落鸟类物种的重要手段。
社区内0.33平方公里的面积,六年来一直是王小波的固定观鸟“宝地”。到目前为止,他已在该群落中记录了174种鸟类,今年又新增了36种。大鸨、黑鹳、草原雕等国家保护动物被他称为社区的“明星鸟类”。秃头鹎、灰椋鸟、灰喜鹊、黑鸟等是小区的“老居民”。
观鸟第六年,王小波仍在不断刷新社区鸟类物种记录。截至今年11月15日,他已记录群落鸟类146种,比去年增加24种。
在北京的一个住宅区,他对鸟类物种的增长速度感到惊讶,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走这条独特的观鸟之路的决心。他还希望未来,城市更多的地方能够出现更多的鸟类。
11月15日,王小波在小区观鸟。新京报记者 王佳宁 摄
途中出家的观鸟者
50岁时,王小波决定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他成为一名观鸟者。当他拍摄鸟类时,他并不太关心照片好看不好看。看鸟的时候,他并不太关心鸟是否漂亮。 “观鸟者的目的是观察鸟类的生活习性,识别并记录鸟类种类的变化。”王小波说。
事实上,50岁之前,王小波从未认真看过鸟。他一直是一个忙碌的办公室职员。他在IT行业从事销售管理工作十多年,习惯用数据和表格来管理事情。

当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时,他决定寻找一种爱好来丰富自己未来二十年、三十年的“退休”生活。 “我从小就热爱大自然,与生物打交道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有限,我无法从事博物学,我必须专注于某种生活方式的事情,将会更加深入。”
经过一番比较分析,伯德成了王小波的最佳选择。 “考虑到现实,我的爱好不可能完全脱离城市生活。与其他动物相比,鸟类与城市的融合有先天的优势。我之前也观察到,雉鸡、雉鸡在我们社区生活得非常稳定。”戴胜、麻雀等鸟类在当时都是非常神奇的。”
那是2014年,王小波决定开始自己的观鸟生涯。用他的话说,“零基础,无指导”。
他的第一次正式观鸟是在山东荣成烟墩角的天鹅湖。
“当我到达那里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很壮观,不是天鹅,而是拍摄天鹅的人。”王小波记得,当时有数千人在岸边架起三脚架,将镜头对准水中的天鹅。他觉得别扭,就独自绕到天鹅湖对岸的湿地,发现除了天鹅之外,还有很多当时他基本不认识的鸟儿。
后来,王小波统计,这次观鸟之旅他一共看到了13种鸟类。正是这次经历让他意识到面对面拍摄鸟类并不是他的兴趣。 “我想从更多角度观察这些野生鸟类在自然状态下的动作、活动和习性。”
2015年,王小波无意中听到在北大附中从事自然教育的发晓提到,即使在北大附中这样闹市中的一个“小地方”,也有80多种物种。鸟类数量已被记录。从地理位置和自然栖息地来看,我的社区比北大附中要好。 “也许你可以在社区里看鸟。”
几十年的工作习惯,让王小波深刻认识到“任何东西都可以骗人,但数据骗不了人”。他翻出了自己在小区里拍的野鸡和戴胜的照片,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数据库,填写了小区里鸟类的种类和数量。从现在开始,我每次看鸟都会记录下来。
半路出家的王小波,认识的鸟类种类屈指可数。刚开始观鸟时,他只是靠买参考书、看图鉴、上网搜索。渐渐地,他认识了一些观鸟朋友,并开始向观鸟专家请教。
“年轻的观鸟者可能会记住一只鸟的很多细节,但像我这样的老年人记忆力很差,只能记住鸟的主要特征,但这足以判断大类别。”对于主要特征非常相似的鸟类,王小波的方法是先拍照,尽量从能看到细微差别的侧面拍照。有的需要把鸟的叫声录下来,然后上网查或者请专业人士进行比较。
时至今日,王小波对于鸟类种类的识别和确认仍然十分谨慎。 “六年来,我在全国各地看到了900多种鸟类。然而,在记录一个社区的新鸟类品种时,必须有照片或录音。虽然大部分目标鸟类都可以通过自己,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还是请观鸟专家祝福吧。”

站在树顶的灰椋鸟是社区中最常见的十种鸟类之一。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社区观鸟就像“密室寻宝”
对于王小波来说,在社区观鸟就像在密室寻宝。
他的社区位于北京中轴线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正北8公里处,面积0.33平方公里。社区原有的南北两大湖区和西北住宅区之间的“神奇森林”(鸟类因栖息地适宜而聚集的森林)是王小波确定的最佳观鸟区。
刚开始社区观鸟时,为了全面调查社区鸟类的分布情况,王小波画了一张全长约4公里的鸟类断面图。
这张“藏宝图”有很多细节。王小波表示,除了尽量少走重复路线外,最重要的是顺流而行。 “如果你逆着光走,鸟儿会先看到你,它就会躲起来,所以你肯定不会看到太多的鸟。如果你逆着光走,鸟儿看不清你,但你却能看到鸟儿。”非常清晰,拍摄效果会更好。”更好的。”
摸清了观鸟黄金地带后,王小波在社区观鸟不再依赖固定路线。例如,如果他听到珍稀鸟类的叫声,他就会集中精力观察附近的区域。 “毕竟我的主要目标是观察更多重点目标鸟类,所以找到‘新面孔’是首要任务。”
据王小波观察,社区观鸟的时间也很有讲究。 “在我们社区,观鸟的最佳季节是春天,春天最好的时间是早上,越早越好。”王小波记得,去年社区录制的第一首《百日》就是第一首凤头鹰。飞行时间是5点35分。

秋季,由于早晨气温较低,鸟类的活动减少,一般只在7点左右日出后出现。 “像现在这样的迁徙季节结束时,我每天7点到7点30分就出去,这样可以赶上鸟类的活跃期。”
相机、望远镜、录音笔是王小波社区观鸟的标准“三件套”。
他认为自己是观鸟者中的摄影师。 “有些人只用双筒望远镜观鸟,自信自己能用肉眼辨别鸟类的特征,但我实在没有这个信心,所以我一直坚持观鸟。如果不带清楚图片,你看不到。”
王小波记录的社区鸟类种类中,有的鸟在他耳边“放声响”了四五次,却很难看见;有些鸟类极其难以识别,因为它们的外观和特征太相似。在这种情况下,录音笔就成了他观鸟的“法宝”。
有一次,王小波在群落里拍到了一只疑似北京平原稀有棕眉莺的棕眉莺,兴奋地将其添加到群落鸟类物种记录中。但回家后仔细看照片,觉得很难与社区中比较常见的巨嘴莺区分,于是王小波就把棕眉莺从记录中删除了。
一位观鸟专家告诉王小波,棕眉莺和巨嘴莺的外貌特征太相似了。在野外进行环带时区分它们的最佳方法是测量喙的厚度。任何超过三毫米的东西都是巨嘴莺。 ,小于三毫米的是棕眉莺。但王小波拒绝置评,相关规定也不允许个人捕捉鸟类。
王小波专门请教了鸟类声音识别专家,试图区分两种鸟类的叫声。当王小波在小区再次发现疑似棕眉莺时,他赶紧拿出录音笔录下了它的声音。结合照片鉴定,他最终确定这是北京郊区海拔1000米左右山区常见的棕眉莺。夏季在北京地区繁殖的夏候鸟。
王小波在社区的鸟类物种记录也增添了丰富多彩的色彩。
一只苍头燕雀在社区的林地里觅食。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星鸟》和《老朋友》
今年秋天,王小波首次在社区记录到黑鹳、草原雕等“明星鸟类”。
“以前北京的黑鹳基本以家庭为单位生活,留在房山十渡地区繁殖,今年西北郊官厅水库也记录到了20只黑鹳。”王小波记录了11只黑鹳。月亮按照猎鹰的迁徙路线飞过社区。据他猜测,那是一只迁徙的雏鸟。
今年10月和11月,该社区曾三次记录到草原雕的踪迹。王小波认为,这是他所在社区观鸟的“高光时刻”。 “因为此前北京对草原雕的监测记录中,基本上每年只有一次目击记录,是北京非常罕见的猛禽。”
打破纪录的成就感让王小波对这些珍稀鸟类出现的瞬间记忆尤为清晰,详细记录了具体的日期和时刻,有多少只,以及它们如何迁徙和停留。
但更多的时候,王小波是在和社区里的“老朋友”打交道。
11月15日早上7点30分,王小波像往常一样扛着5公斤重的“大炮”走出家门,首先沿着南部社区步道进行观测。
镜头中首先出现的是灰椋鸟,它是社区中最常见的十种鸟类之一。 “灰椋鸟脸上有一些白色斑点,喙尖,呈橙红色,主要吃草籽,喜欢睡在树干上,还喜欢与灰喜鹊、珍珠颈斑鸠混居。”去觅食。”王小波说,到秋冬季节,群落中聚集的灰椋鸟数量可达60只左右。
小区内最佳观测位置是芦苇丛生、水草环绕的东南湖。 “南湖尽管水位低、面积小,但却是珍稀鸟类喜爱的地方。”他说,已经记录到了共轨鸟和白胸苦鸟等不常见的鸟类,还有芦苇莺和巨嘴柳。莺、鹀等小鸟也经常到此栖息。当普通朱雀经过时,它们也会休息并以周围的植物为食。
前一天早上,王小波还在南湖看到了一只白腰草鹬。 “这种鸻鹬鸟对水深的要求非常高,如果水太深,它就只会到像这样的小水坑里觅食。但夏天在昆明湖的深水中就很难看到它了。”宫殿。”
与南湖相比,社区内的北湖热闹得多。这里是留鸟的天堂。黑水鸡和小鸊鷉全年在此繁殖。白头鹎喜欢在芦苇上荡秋千。成群的画眉、灰喜鹊、珠颈鸠、麻雀在湖边的草地上觅食。
王小波分析,这是因为与南湖相比,北湖水域面积更大,水位也相对稳定。有水生植物可供鸟类栖息、繁殖。湖岸人工与野生草本植物的结合,为鸟类提供了大量的草籽和其他食物。
今年9月,王小波还在社区救助了一只四声杜鹃幼鸟。 “这种鸟的幼鸟是巢寄生的,四声杜鹃把蛋产在灰喜鹊的巢里,灰喜鹊为其孵蛋,并喂养和保护幼鸟。”
有一天,其中一只小鸟撞到了社区一所房子的玻璃窗,摔在了地上。王小波接到消息后,前去查看、喂食,并致电北京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对小四音杜鹃进行救助。
他说,另一只带着它的小杜鹃在小区里一直待到十月份,直到天气变冷,小四声杜鹃消失了。直到现在,王小波仍然怀念这只孤独的小四声杜鹃,“不知道它能顺利到达南方吗?”
一只黑鸟正在社区里吃柿子。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鸟类迁徙的“城市路径”
六年后,王小波本人对社区观鸟的结果感到惊讶。
截至目前,他所在社区已记录鸟类174种,涉及20目49科,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大鸨、黑鹳2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2种。野生动物,如草原雕和黑鹰。 。

据王小波统计,174种鸟类中,有近110种在群落中短期停留,约占60%;停留时间较长的21种,约占12%;通过群落迁徙的有40种,约占23%。此外,还有一些居住类型复杂或者在周边地区的活动有记录的。
近三年来,社区整体观鸟数据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
2018年、2019年和2020年,群落分别记录了29种、31种和36种鸟类新种,增幅较前三年近一倍。截至今年11月15日,他已记录该群落鸟类146种,占近六年鸟类总数的84%。
王小波认为,群落中记录的鸟类种群和数量之所以不断增加,不仅与自己观测水平的提高有关,也与群落环境的改善有关。
“我们小区原来有南北两个大湖,北湖约4万平方米,南湖3.4万平方米。据老居民介绍,前几年湖里有很多水草、芦苇。多年来,吸引了多种水鸟,最多的达到百余只。”王小波说,后来,由于失去了水源,两个湖终于在2010年干涸了。
2015年,社区干湖开始整治。改造完成后,社区集中绿地面积约8万平方米。经过两三年湖区植被逐步恢复,初步形成了较大面积的人工小树加小面积湿地生态以及一些人工与野生草本植物相结合的绿地。
在他看来,如此丰富的栖息地保证了群落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能被植被良好覆盖,为鸟类提供了合适的栖息地。
这几年,王小波还陆续观察到以凤头雕为代表的猛禽候鸟在社区上空飞翔。这启发了他也许观察猛禽在特定时间沿着相对固定的路线迁徙。
2019年5月13日,王小波像往年一样早早收拾好装备出门。不久之后,一群凤头鹰出现在社区上空,不久之后,又有两三只燕隼飞过。那天,他陆续观察到了110只猛禽,社区迎来了第一个“百猛禽日”。
王小波突然意识到,社区里有一个观鸟的大日子(迁徙高峰日)。这个发现让他兴奋不已。
从今年春天开始,王小波开始对社区里的猛禽进行更加系统的观察,同时也开始关注小型候鸟。
今年5月10日,他观察到有1000多只鸟飞过社区,其中普通朱雀约占一半,数量较多的还有小鹀、树鹨、黄鹡鸰等。这一天,王小波还记录了新的鸟类。群落中的鸟类,如绿鹭、白腹燕子和栗鹀。
“白腹燕子在我国西北、东北地区比较常见,在北京应该是一种罕见的候鸟。”一个关于鸟类迁徙的“城市路径”的猜想逐渐在他的脑海中形成。

11月16日,王小波和鸟友们在官厅水库附近的湿地发现了一只竖条纹小猫头鹰。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照顾好家门口的鸟儿”
从卫星图像看,北京北部有一条明显的绿色走廊,宽约两公里。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向北有东小口森林公园、太平郊野公园、班塔郊野公园,林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王小波的小区正好位于这条绿色通道上。
据王小波观察,喜欢沿着这条“城市路径”迁徙的猛禽数量大约是喜欢沿着京西山区主要迁徙通道迁徙的数量的5%-10%。
据长期从事鸟类学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张正旺介绍,鸟类迁徙路线相对固定。有些鸟类习惯于从山区或郊区迁徙,而有些鸟类则更喜欢飞越城市上空。迁移。 “如果遇到大的障碍,鸟类可能会改变迁徙路线,但城市建筑物的高度对这些鸟类来说并不是障碍,它们可以飞到数百或数千米高。”
张正旺分析,无论是社区还是公园,吸引鸟类留在城市的主要是能为它们提供供给的觅食地和生活环境,让它们在迁徙过程中补充飞行所需的能量。
他介绍,几十年的监测调查表明,北京鸟类的多样性不断提高,数量也大幅增加。 “20世纪80年代,北京有300多种鸟类,后来增加到400种,现在已经达到500种左右。”
但他也承认,一个群落或地区记录的鸟类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适合鸟类停留和生存的生态位的形成或完善。但能否反映整个城市生态环境的变化,还需要更多的调查和监测。 “如果城市中有更多的区域能够提供类似的标志或数据,就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城市的生态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鸟类留下来。”
张正旺也认为,未来城市改造时,应尽可能为鸟类提供一些栖息地,人类不要过多干扰它们。 “比如建设绿地时,最好注意结构合理,包括乔木、灌木、草本植物,并提供一些水源。”
对于已经在社区观察记录了6年并且依然乐在其中的王小波来说,他期待着越来越多的鸟儿入住,他也想好好照顾眼前的鸟儿。
他觉得全国观鸟组织联合行动平台(“朱雀俱乐部”)创始人钟嘉有句话特别好,“照顾好鸟儿,照顾好家门口的鸟儿”。 “第一通电话是第四通电话,第二通电话是第一通电话。”王小波解释说,这意味着让小鸟愿意在家门口休息、停留,并照顾和保护它。
因此,他觉得保护家门口的鸟类栖息地是他的责任。他希望未来的城市景观和生态建设能够为鸟类和其他动物留下一些生存空间,让它们愿意并且能够与城市中的人类和谐共处。
“真正美丽的城市景观,不仅要有‘花香’,还要有‘鸟语’。”王小波说。
新京报记者 吴娇英 摄影记者 王佳宁
陈思主编、吴兴发校对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联系本站,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jnpharmart.com/html/tiyuwenda/13358.html